
“病菌在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成为该书在疫情后再次走红的关键,书中关于病菌的描述确有许多“意想不到”。
事实上,近代史上包括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等等“人类杀手”,都是由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也是形成今天全球范围人类社会格局的一只“无形之手”。
比如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人占领美洲除了靠枪炮杀人,被一同带去的病菌,成为让更多美洲土著死去的原因;比如皮萨罗1531年带着168人登陆秘鲁征服当地百万人,也不全是因他的机智与果敢,更重要的是早他一步进入印加帝国的天花病毒,让这里陷入内战,疏于防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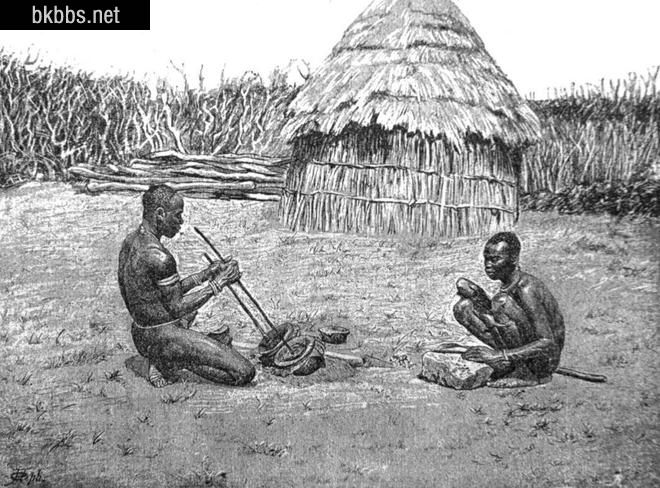
与戴蒙德对话的过程中,他再次给出了一个看待病菌的新视角——相比于死亡,此次疫情的重大影响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一个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的全球性问题。
如果说阅读《枪炮、病菌与钢铁》像一场旅途,那么“人类社会历史轨迹由自然环境决定”这样的结论,显然只是沿途风景中的最后几帧画面而已,更精彩的部分,对每个人而言应该都有所不同。
比如重现病菌的历史,让不少人可以用更开阔和深远的视角去看待当下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于我而言同样引人深思的,则是在公元前8500年促使肥沃新月地带的居民从狩猎-采集转向务农的那个决定。
因为这其实可以视为今天人类社会一切不平等的来源,而这种生活方式转变后,从戴蒙德的角度来看,作为农民这一角色的人类,不论健康状况、寿命还是拥有的闲暇时光,大体上都并不如曾经以狩猎-采集方式生活的居民。
除了充实的知识储备和潜心深入新几内亚原始部落生活的珍贵经历,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之所以受到如此多读者的推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是一本不带种族色彩的专著,让不同肤色不同国别的读者,都能够心平气和地从一个共同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
在那之后,戴蒙德著于2005年的《崩溃》,探讨的是为什么有的社会实施愚蠢的政策而走向自我崩坏,有的社会则可以维持兴盛数百年之久。
其中关于玛雅文明的消亡,维京人的没落,波利尼西亚社会的崩溃,既让我们对其曾经创造的文化和遗址发出由衷感叹,也提供了灾难性决策下最现实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以血淋淋的警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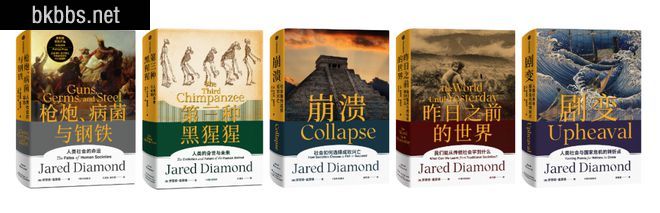
再往后的《昨日之前的世界》(著于2012年)、《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著于2014年)和《剧变》(著于2019年),则可看出戴蒙德越来越多地将目光从人类社会的演变历史,转移到国家兴亡的话题上来。
如何理解这样的转变?或许从戴蒙德的经历中可以寻得答案。
02、转变
能写出这样一系列跨越不同宏大主题的作品,与戴蒙德与众不同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1937年出生在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戴蒙德成长于一个带给他无限收获的家庭。
他的父亲出生于俄罗斯,后来随父母移民美国;外祖父母出生于东欧,在19世纪80年代移民美国,之后生下了戴蒙德的母亲;他的丈人和丈母娘则在早期从波兰移居美国,之后生下了他的妻子玛丽。
家族成员源自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洲的背景,让戴蒙德有这样一个最初的契机,意识到人类在地球上的轨迹变迁。因为母亲是语言学家,戴蒙德从3岁开始识字,到16岁已经陆续学习了英语、拉丁语和德语,因为父亲是医学家,他从小立志成为医生,后来考入了哈佛大学。
到此时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家庭给戴蒙德带来的影响,但后来的人生轨迹中,越来越多个人兴趣和经历似乎对他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同样有许多是忙碌于生活的大多数人,大概率一辈子也不能拥有的体验。
比如在大四那一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正想从事的其实是科学,便转而攻读生理学这门实验室科学的博士学位,研究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身体机制,且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

在欧洲的生活,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和自己拥有截然不同童年的朋友——他们经历过二战期间炸弹从天而降,有的也因此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还有的看到过身边的人就此因战争死去。

